
第二节 裴頠的《崇有论》和欧阳建的《言尽意论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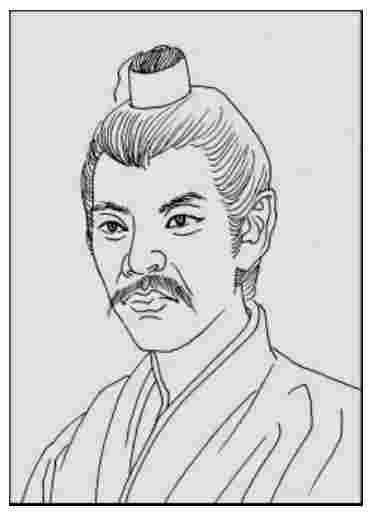
裴頠像
裴頠(267?—300年)字逸民,河东闻喜(今属山西)人,曾任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等职。常与乐广“清言”,以善言“名理”为时人所推重。但就其思想倾向而言,他不在玄学家之列,史书称他曾“奏修国学,刻石写经”,精通儒家的“郊庙朝享礼乐”,并说他“深患时俗放荡,不尊儒术”,乃著《崇有论》,批评何晏、阮籍“口谈浮虚,不遵礼法”,王衍等人“不以物务自婴(婴,同撄)”。可见,裴頠是一位研究儒学的学者,他是为了维护“名教”的利益而评论玄学的。后因反对赵王司马伦的贪暴而遇害。
裴頠《崇有论》的基本观点,是反对何晏等人的“贵无贱有”之论,认为“无”不能生“有”,“有”为“自生”。他指出:何晏等人“阐贵无之议,而建贱有之论。贱有则必外形,外形则必遗制,遗制则必忽防,忽防则必忘礼,礼制弗存,则无以为政矣”。这是说,因为形体是“有”,贱“有”必然放任形骸。放任形骸必然遗弃制度规范,遗弃制度规范必然没有防范措施,以至达到狂放无礼的程度。在他看来,礼制不存,将危及封建主义统治。这是他反对“贵无贱有”的主要原因和《崇有论》的立论宗旨。
为了说明“无”不能生“有”,他依自己的观点解释《老子》,以求驳倒“贵无贱有”的理论根据。他说:《老子》一书虽然“以无为辞”,讲了一些关于“无”的词句,如“绝圣弃智”“绝仁弃义”“绝巧弃利”等,“而旨在全有”,意在收到“民利百倍”“民复孝慈”“盗贼无有”等实效。若将老子学说看成是“以无为宗”,则是片面的见解。他用《礼记·乐记》中节欲养生的观点理解老子所说的“无”是“于无非无”,即对物欲有所节制,表面上看是有所亏损,其实是更好地保全了生命。“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”,“无”只是“有”的一种表现形式,所以他说:“夫至无者,无以能生,故始生者,自生也。自生而必体有,则有遗而生亏矣。”这是说,“无”不能生“有”,事物从它始生(最初产生)时起就是自己生出来的,如果要给它再找一个造物者作为它的依据(体有),那么不但“有”会受到损失(有遗),事物也不能成其为事物了。
为了说明“无”不能生“有”,裴頠还提出“济有者(即成全有的)皆有也”的命题,从事物的互相依赖上剖析“贵无贱有”不符合实际。他与郭象虽然都反对“贵无贱有”,但郭象所说的“有”是无条件无原因的孤立存在,因而带有不可捉摸的性质。裴頠则认为,事物有不同的类别和性质,每一类别各有其偏,“偏无自足,故凭乎外资”,因而它们互相依赖。事物是有,促成事物的条件也是有,如果否认条件的存在(如郭象那样),或把条件看成是“无”(如何晏那样),都是不符合实际的。他举例说:“心非事也,而制事必由于心。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,谓心为无也;匠非器也,而制器必须于匠,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,谓匠非有也。”这是说,思想(心)不同于事物(事),但判断事物必须以思想为条件,不能因为判断事物的思想不同于有形的事物,就认为思想是无。匠人不同于器皿,但制造器皿必须以匠人为条件,不能因为规划方圆的匠人不同于方、圆的器皿,就认为匠人是不存在的。他还说“欲收重泉之鳞”(捕鱼),不是“偃息”(静坐)所能得到的;“陨高墉之禽”(猎取高墙上的鸟),不是“静拱”(袖手)所能成功的;“审弦饵之用”(运用弓箭和钓饵的技术),不是“无知”所能掌握的。总之,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“有”而不是“无”。
裴頠在肯定“有”的绝对性和普遍性的基础上,进一步分析了“道”与“有”的关系,认为“有”是真实的存在,“道”只是对“有”的综合与概括。他说:“夫总混(总合)群本(万有),宗极(最高)之道也。”“道”是万有的总合,离开万有,就不会有“道”。这就从名和实的关系,说明了“道”与“有”的关系,从而否定了何晏等人关于“道”(无)的本体观念。
此外,裴頠还批评了无为的寄生思想,主张“分地之利,躬其力任,劳而后飨”,即利用自然资源,通过生产劳动,谋取人的生活资料。在养生问题上,他反对纵欲和禁欲,从珍惜生命的观点提出节欲的主张。
《崇有论》发表以后,受到王衍等人的反驳,虽“攻难交至,并莫能屈”。当然,由于裴頠和郭象都反对“贵无贱有”,所以他们的观点也有某些相通之处,如用“有”来表述一切事物和现象,把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等同起来;肯定“贵贱”等级的合理合法,以保护“名教”不受损害等。故就他的思想理论高度而言,要比同时代的欧阳建逊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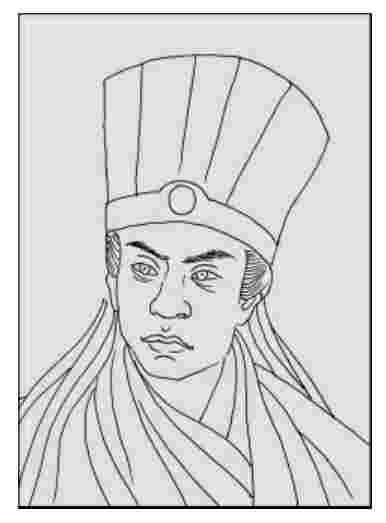
欧阳建像
欧阳建(约268—300年)字坚石,渤海南皮(今河北南皮东北)人。出身于冀州大族,历任山阳令、尚书郎、冯翊太守等职。名气很大,当时人称他为“渤海赫赫,欧阳坚石”。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,人们都很惋惜。
欧阳建的《言尽意论》是讨论名和实、言和意关系的一篇论文。“言意之辨”是玄学中重要的争论问题之一。这个争论和“声无哀乐”“养生”问题的争论,曾被称为玄学中的“三理”。当时关于言意问题的辩论,有两种对立的意见:一种意见主张言不尽意,以何晏、王弼为代表,他们看到了语言、文字只能近似地反映真理这一事实,但又夸大了这种差别,把不完全性曲解为不真实性,得出认识真理必须忘掉语言、文字的错误结论。嵇康的“声无哀乐”也属于同一类性质。另一种意见主张言尽意,以欧阳建为代表,他的思想是对汉魏之际名法思潮的继承和发展。
《言尽意论》取题于《周易·系辞上》:“子曰:圣人立象以尽意,设卦以尽情伪,系辞焉以尽其言。”其主要论点是,事物及其性质是客观的,不以人所设的名(名称、概念)、言(语言)为转移。他说:
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,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,然则名之于物,无施者也,言之于理,无为者也。
这里他认为名和言都是依据事物及其属性而确定的,例如,事物有方、圆的形状,人们才会有方、圆的概念;事物有黑、白的颜色,人们才产生黑、白的概念;概念对于事物,并没有给予什么;语言对于事物的道理,也不能有所改变。总之,是事物及其性质决定了名、言的内容,而不是相反。
欧阳建进而从名、言的作用上论证它们对事物及其性质的依赖关系。他认为“诚以理得于心,非言不畅;物定于彼,非名不辨。言不畅志,则无以相接;名不辨物,则鉴识不显”。语言的作用在于表达事物的道理;概念的作用在于反映事物的区别。如果语言不能表达思想,人们就无法互相交流;概念不能反映事物的区别,人们的认识能力就不能显现。因此,有什么样的物,才有什么样的名;有什么样的理,才有什么样的言。名、言和物、理是一致的,而不是分离的,其间的关系犹如“声发响随,形存影附,不得相与为二”,由此他得出结论,既然名、言与物、理是一致的,那么,名、言就能反映出事物及其性质的真相而“无不尽”,从而把名实关系的讨论从“名副其实”推向名能反映实的高度,丰富了古代的理论思维。
上一篇:城市仿真系统关键问题研究
下一篇:白血病也不一定要换骨髓





.jpg)
.jpg)
